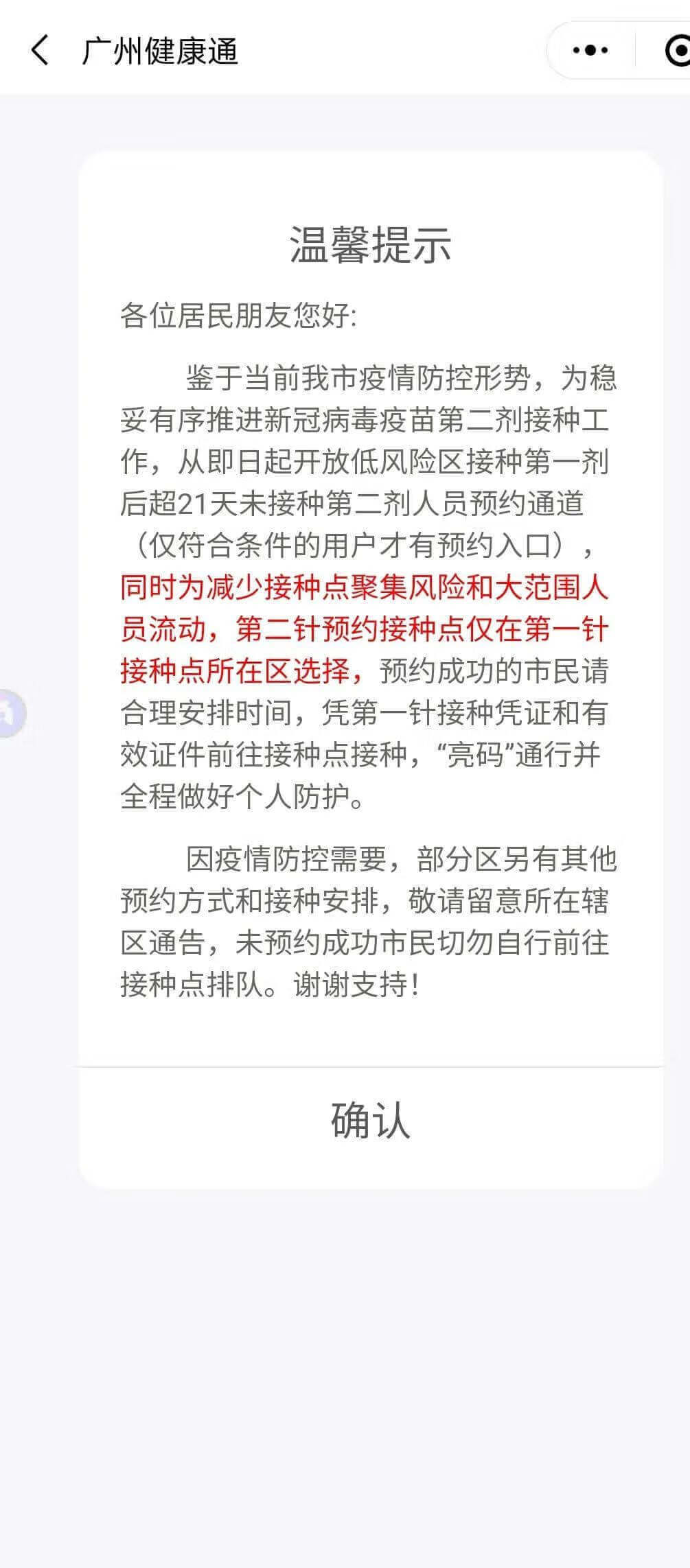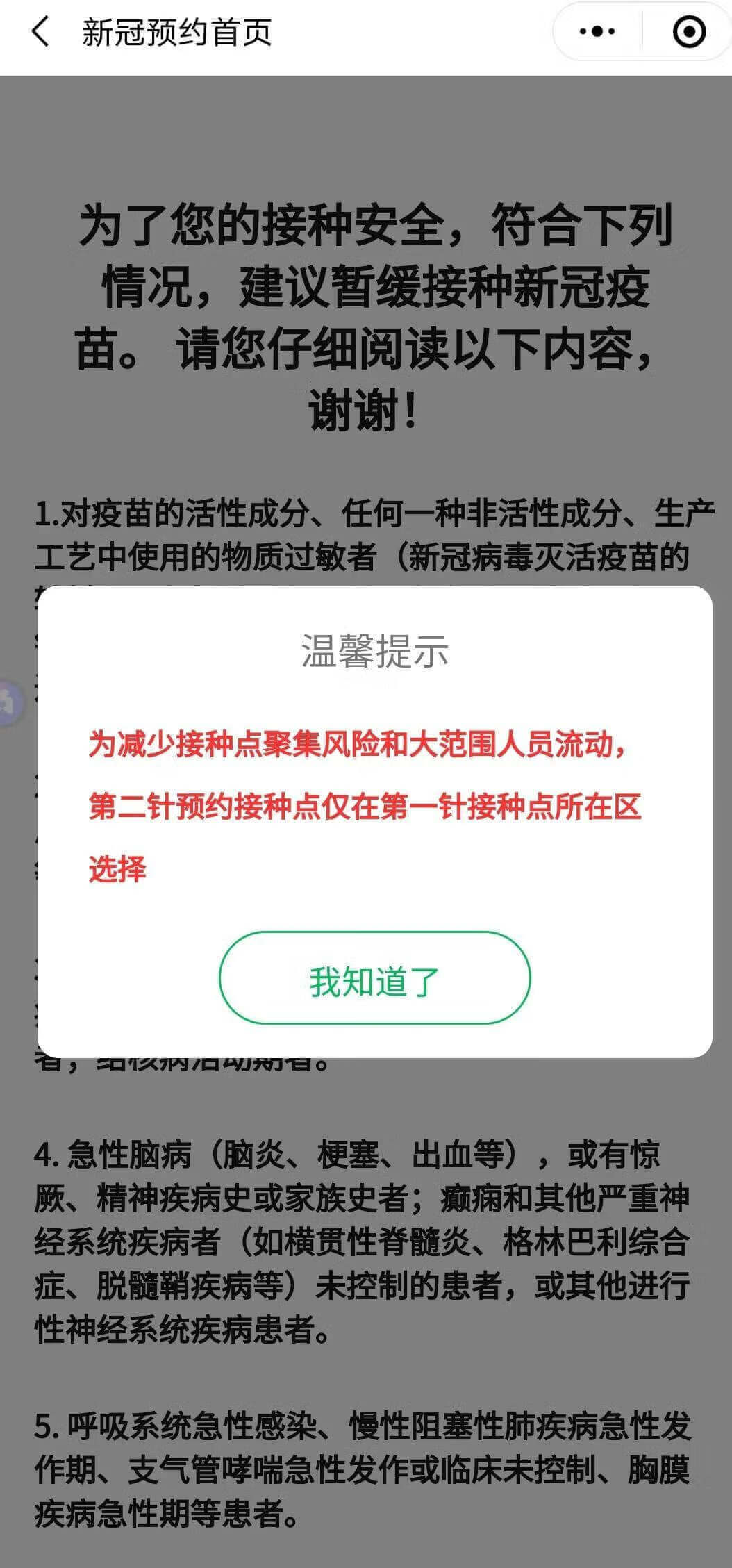.jpg)
昨天,和姐姐视频聊天,问询起了父亲年少时期的一些事情。说到为难处,姐姐忍不住又开始哭了,边哭边说,边说边哭。说着说着,姐姐在讲述父亲年少时的一些艰难时,也不由自主地把说起了自己年轻时的不容易, 谈不上是牢骚。但我其实,多少年来,也很想为已经六十多岁的姐姐写篇文章,记述一下她这不容易的一生。为啥没写?因为,我有些顾虑,我担心写不好了,姐姐又会把我数落个没完。我也知道,姐姐此生,爱较劲,和别人较劲 ,也和自己较劲。
(一) 姐姐的童年
姐姐出生于一九五六年,比共和国晚了几岁。
父亲和母亲婚后的第二年,生下了姐姐。生姐姐时,母亲还上了晕,应该就是现在说的血压高了,是四爷爷找老娘婆,也就是接生婆,想办法,有惊无险,生下了。
姐姐,从小脸就长,还有些发黄,但鼻梁很高。父亲结婚那年,决心和四爷爷分开过了。四爷爷入了合作社了,而父亲没有,自己包了些地,和母亲二人犁地、播种、夏天一起锄地,自己收,到秋天,收成居然不错,打了一炕的粮食。因为没柜子和瓮盛放,只能堆在炕上,留下一条窄窄的位置,用于睡觉。
后来,父亲出去,赶车到集宁拉煤,走了一些时日,回来发现,炕上的粮食少了不少,就质问母亲,粮食哪里去了?母亲清楚,但又没法说出真实缘由,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就编了个谎,说是被耗子盗的吃了。
在姐姐出生了七、八个月,当年快入冬时,已早早出嫁的大姑,建议父亲,“咱妈走时,给你攒了不少财物,都给你留着呢。你还是去找咱妈妈去吧。毕竟咱妈是亲妈呀。”
其实,父亲对奶奶是有很大的成见的,自己这些年,是自己的四叔把自己拉扯大的,也张罗着帮自己把家成了。虽没有生育之恩,但养育之恩更浩荡,自己一下子离开了,于四爷爷那边,父亲有些于心不忍。于是,父亲和四爷爷掏心至肺地进行了商量。四爷爷觉得自己的侄子也成人了,自己这些年也尽到力和心了,遂同意父亲的决定。
于是,姐姐在八个月大,还在吃奶时,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颠沛和流离。一路的马车上,姐姐在母亲用破被子围卷成的襁褓里,就着已入冬的冷风,一直哭个不停。
父亲计划得挺好,守着奶奶。毕竟是自己的亲娘,好歹有个帮衬。但事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奶奶一九四二年,改嫁到补龙湾村后,是到了一位黄姓人家,老汉是给一个熬土盐的场子看场子的,说白了,就算是长工吧。家里穷得很,也没啥家业。是奶奶拿出了之前攒下的部分银元,购置了一些土地,后来,日子也渐渐过得好了。也算是,老黄家跟着沾了光了。然后又生了叔叔和姑姑。
父亲刚到补龙湾村时,没处去,就暂时住在了奶奶的院里。好在那时,叔叔和姑姑年龄都还不大,也没成家呢。一大家子人在一起,尽管奶奶的后老头不是很乐意,但因为父亲已独立,母亲也很勤劳能干,为人也和善,倒也相处得其乐融融,谈不上多好,倒也过得去。
叔叔比父亲小六七岁,姑姑比父亲小十岁,尽管那些年一直没在一起,但有位大哥在家,也很开心。而因为父母天天在忙,姐姐就经常和奶奶在一起,晚上也跟着奶奶一起睡。奶奶也很疼这个孙女,有点儿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也就给了姐姐了。
在一起住了四五年的时间,也是姐姐小时候最快乐、最无暇的时候。特别是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时,各家砸锅,甚至把用作农具的含铁的东西,都砸了,进行再炼钢,以便使国家的钢产量“三年赶英,五年超美”。父亲给生产队的车队赶大车,整天奔忙在外,又好赌钱,有时候好久不回来一次。母亲在生了一个儿子后,因自己照看不过来,加上赌父亲的气,没几个月,就早早地夭折了。待父亲隔年赶车回来时,问母亲,“儿子呢?”母亲只咬牙回了一句,“你还知道有儿子?早死了!”父亲无言,自知也理亏。
但在叔叔娶了婶婶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婶婶很霸道,又能挑理找茬,沾光不吃亏,和公公婆婆合不来,和小姑子也合不来,和我的父母,这个后儿子一家,就更难合得来了。
没办法,父亲只得搬出来了。搬到哪里去呢?找人打听,最后在六零年的六七月间,也就是国家上下,包括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还苏联债的时候,被迫选择去了同属一个大队的张林村,买了人家两间房。和一家姓郝的人家,当时在大队是个干部,住到了一个院里。
没粮食吃,人们饿得连树皮都剥完了,最后没法,父亲从地里,割回扁珠珠草,一种野地里喂猪的植物,在锅里炒了,然后,再放到碾子上压碎,和成面,蒸成饼子吃。吃的人们不是肚胀,就是面黄肌瘦。姐姐天天饿得“哇哇”哭,其实,不光孩子们不好受,大人们也没法,吃啥?根本就没得吃。当然,情况也不尽然,在塞北的地里有收成,但国家有令——用于偿还外债,国家荣誉高于一切,谁也不敢违反。所以,那三年,加上不少地方闹自然灾害,不少人干着活儿时,就栽倒了,再也没起来。
姐姐天天哭个没完,而母亲又奶着二姐,几乎没啥奶水。父亲听着觉得烦透了,尤其是晚上好不容易把姐姐哄睡着,到后半夜就又哭醒了,谁哄都哄不住。气得父亲只骂,“你个妨祖货,嚎丧鬼,怎么还没完没了啊?”。有一次,半夜里两三点,父亲实在气不过,揍了她两巴掌,把姐姐扔到了当院里,并把门从里边插上了。这下,姐姐迷迷瞪瞪的,看着外面黑黑的夜,就更怕了,哭得更厉害了。但怎么哭,父亲就是不给开,母亲也拗不过他,眼睁睁地看着闺女在院里把嗓子一直哭哑了。后来,姐姐自己爬上窗台,把糊窗户的麻纸,都扯烂了。于是,姐姐又少不了父亲的一顿胖揍。
过了几天,叔叔套着车,来张林村东边拉土,姐姐跟着去了,到了奶奶家。奶奶家有些存粮,姐姐去吃了几顿饱饭。临回来时,奶奶又给她拿了两个糠窝窝,就是用糠与白面做的。姐姐舍不得全吃完,只吃了一个,另一个留给了哺乳期的母亲,但母亲抿了抿干瘪的嘴唇,咽了两口唾沫,嗓子只是动了动,眼里含着泪,没有吃。她把那唯一的一个糠窝窝留给了姐姐,待她饿了吃。
后来,父亲和奶奶说起姐姐总哭个没完的事时,奶奶说,“兰子在我这里不哭呀?总是一觉到天亮呀!”姐姐的小名叫兰子,二姐叫二兰。
是啊,那时,姐姐哭,不是因为别的,是饿得难受,饿得睡不着,是父母忽略了她的感受。
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姐姐会饿死的。于是,父亲想了个主意,主动揽了大队里放夜牛的活计。趁着夜里没人,父亲就偷偷地把正长在地里的山药蛋从地下抠出来,蔓子还留在上边;把黍子,麦穗用手撸下来,用麻布包着,趁人们都入睡的时候,到了家里的窗户底下,轻轻地敲三下窗楞,算是暗号。姐姐耳朵灵巧,没待母亲反应过来,就起身轻轻地把门开开,让父亲进来。一家三口,也不敢开灯,趁着黑,把柴棍清理清理,用擀面杖把壳擀掉,收起来,当吃的。
因为父亲老这样,同院里住着的郝姓老婆,不免有些警觉。总是在父亲弄吃的回来时分,起来到院子里尿泡。这样,父亲就得更加小心谨慎了,因为弄不好,一旦被发现,那可是要挨整的,弄不好,就很容易被定个反革命,或四类分子的。
不是很饿了 ,姐姐也不再老哭了。
(二) 有个好赌的父亲
姐姐,早早地,就懂事了。
帮母亲洗尿布,拾地里的麦穗,帮母亲哄二姐。
父亲很能干,也有头脑和决心,就是好赌。
在母亲怀二姐的六七个月里 ,父亲赌瘾又上来了。编了个理由,套车把母亲送到了姥姥家。然后,用自己家的地方,招呼大队里好赌的人们来家里,人家赌,他没钱,旁边看着。待一场快结束,决出输赢时,他收打罐钱(类似于抽成)。连着两天,他收了有二三十块钱,对于赌红眼的赌徒们来说,这也不算个事。
但在第三天晚上,他实在手痒痒的不行了,上去押了三宝,结果,不光把之前收的那二十来块输了个精光,还欠下二百多饥荒。那时的二百多,可就是个钱了,砸锅卖铁,拆房子,都还不清。
这下傻了。连着熬了几天夜,加上输了钱,不甘心导致的气火攻心,父亲一下子,病倒了。连着几天,昏迷不醒。四爷爷,大姑都去了,最后请到一位公社里的医生,好像叫闫廷佐,输了几天液,算是搭救了他一条命。
从那次起,父亲觉得没脸见人了,也是为了躲债,起身去县里的煤矿,下了窑。算是洗心革面了。
作为姐姐,虽年龄不大,因为在那个讲究家族势力的年代,本就势单力薄,招人看不起,又有一个嗜赌成性的父亲,更招人唾弃。小时候,姐姐没少和人家孩子们嚷架,哭个没完。
父亲好赌到了什么程度?
在和母亲一起推碾子时,听说哪家有人耍钱,他就编个幌子,偷偷跑去了,把母亲一个人留下推着碾子。
说来,更早之前 还有一次,因为父亲给队里赶大车,奶奶就交代父亲,再去商都那边时,有奶奶嫁出去的妹妹在。奶奶改嫁前,为了转移财产,就借给嫁出去的妹妹五百块钱。过了这么些年月,奶奶想要回来。就让父亲赶车路过时,记着把借的款要回来。
是的,父亲是要回来了,人家那边也如数给了。但他在回来的途中,白天赶车,晚上爬到押宝场,连着几夜,就输光了。心疼、惋惜、不甘心、没脸见人、愧疚,但无论如何自责,输出去的钱,是要不回来了。
回来后,父亲没敢告诉母亲,也没敢告诉叔叔和姑姑,只是偷偷地和奶奶说了,还特别叮嘱奶奶不要说出去。这事,奶奶封口了好多年,直到临死时,才告诉了叔叔。
于是,在七七年,父亲去世后,婶婶还在骂,还在催要,“活该的!真是棺材里伸出了头,死不要逼脸!”
为了保住父亲死后的尊严,姐姐放泼地和婶婶嚷,嚷完了,回家里,又使劲地哭一顿。
(三) 农业社的繁重劳动
姐姐十二虚岁时,就开始独自担水了。到十四岁,就在农业社里,挣一个成年人的工分了。
那时,父亲在煤矿下窑,不经常回来。母亲操持家务,但身体也不是太好,大哥、二哥年龄又小,姐姐早早地,就开始学着挑起了劳动的重担。
水桶是木头做的,四周,还钉着宽宽的铁箍,很沉很沉的,再盛满水,就更沉了。一个女孩子家家,尽管个子长得比同龄人高些,但毕竟骨头还没长硬呢。刚开始,在井台上,不太会使扁担,水桶总是盛不满,就一遍又一遍地练;肩膀吃不住一担水的重量,就挑一截,歇一会儿。当路上遇到熟人时,看她这么小就开始担水了,不无忧虑地说,“女子家家,不怕沉啊?再说,井台那么危险,也不怕掉进去啊?”
每每听到这些话,姐姐就止不住地哭了起来,越是哭,越是咬牙,越是坚强。从那以后,家里吃水,就是姐姐的事了。
再大一些,姐姐看着家里没啥劳动力,就加入了农业社里的成年人劳动了。早晨起来,帮家里做好饭,再喂了猪。然后,就急匆匆地奔向了社里,和大家一起种地、锄地、起粪堆,拾山药、割地、收秋、还有打谷场里的各种忙乎。中午,完工时,还得往家里拔猪草、背柴火。那时,二姐八九岁了,看着姐姐太辛苦,就经常下了书坊,帮着姐姐一起干点。至今,姐姐还一直想着二姐的好,可惜的是,二姐在十三岁时,不幸地走了。
回了家,母亲因为身体不好,除了打针,就是在炕上躺着,也忘了为姐姐做顿饭。于是,姐姐又赶紧烧水、洗锅,张罗着做饭。那时,看着人家同龄的女孩子悠闲、好打扮,姐姐经常止不住地流泪,埋怨妈妈的懒惰和狠心,不理解她自己的苦。所以,免不了就会和母亲吵几句,吵着哭,哭着吵,吵完了,还得接着干。
因为家里的家务太多,所以,姐姐早晨出工,经常会迟到,于是,她晚上睡觉,经常连衣服也不脱,怕起晚了。就这样,还是经常遭到生产队队长的痛骂,“别人都能按时到,就你家是个有事的?”姐姐没法,只有无奈地哭着,是附近住的人,帮她做了解释,“队长,你是不知道,兰子也够可怜的,做了家里的,做队里的,也没个帮手,太不容易了!”
说出来,都有些想哭,那些日子里,几乎都到五月了,人们都换单衣了,但姐姐还穿着没有里子的大棉裤,里边的虱子,都成了集团军了。因为咬的不行,姐姐脱下了棉裤,虱子实在捉不过来,就用石头砸,最后一直把棉裤的棉花,砸得血红。
按说,母亲该帮她干些。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无奈。在怀大哥,临盆要生产时,肚子疼的厉害,让姐姐去叫奶奶来。奶奶也是觉得母亲可怜,就想偷偷拿块肉,给自己的儿媳妇补补身子。但被黄老汉看到了,除了把肉夺了出来,还踢了奶奶两脚。他认为,“自己的儿子还没吃呢,怎么能给后儿媳妇呢?”
奶奶也做不了老汉的主。所以,当母亲看到着急赶来的奶奶,脸色不对时,就问,“妈,你怎么了?”奶奶一直说着没事,是多嘴的姐姐和母亲说了奶奶该打的事,母亲一下子惊住了。生了大哥后,连着几天,不吃不喝,不停地呕吐。再加上后来二姐的不幸夭折,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从那以后,母亲的身体,就一直不好。她也有她的苦衷。身体不舒服,心里也烦躁,实在没心情去帮姐姐干活儿。
(四) 姐姐的拯救
大哥记事后,有一次,和姑姑家的闺女、叔叔的闺女,还有村里另一个男孩子一起玩时,玩到快中午时,叔叔把姑姑家的闺女和那个男孩子留下了,因为那天叔叔家杀了羊,要吃羊肉。唯独没留大哥。
当大哥噘着嘴回到家,父亲问他为什么不高兴时,大哥唯唯诺诺地说出原委后,父亲急了。
“好你的!还兄弟呢?我儿子也只是一个孩子,你就这么看人下菜碟啊?”
父亲把家里仅有的一只羊捉住,拿绳子绑了,死活要杀了。姐姐哭着,反复劝,也无用,就给父亲跪下了,“大大,咱家就这一只羊,我们都指着它能在来年春天时,剪点儿羊毛,下个羊羔,卖个钱呢。而且都怀上小羊了,你别杀它了。求你了!”但为大哥出气心切的父亲,最终没有听姐姐的建议,硬是把那只羊杀了。等杀了,挑开肠肚时,发现大羊肚子里的小羊,已经长出绒毛了,没几天就该生了。可惜,姐姐的眼泪,没能止住父亲的杀戮,也最终没能挽救了那只羊被杀的命运。
姐姐二十岁那年,父亲病倒了。其实,那时,父亲在下煤窑十来年后,已转成了正式工,并正式调到了矿上了,不用再下窑了。但因为奶奶的遗传,父亲是乙肝病毒感染者,加上常年劳累,还有他输钱后造成的心里不顺,发展到了肝硬化,而且是晚期。这一次,又是姐姐,陪着父亲在县里医院,张家口市里医院看病。
在父亲弥留的日子里,他表现得依然坚强。肚子胀,吃不下东西,就自己在肚子上勒了两根腰带;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也不愿让人搀扶。是姐姐,一次又一次地搀扶他,起来,喂水喂饭。上厕所,姐姐怕父亲摔倒,也要跟进去,尽管父亲不停地厉声呵斥她,“你个女孩子家,哪里都有个你!这是男厕所,知道不?”但姐姐还是哭着,不顾一切地跟了进去。
姐姐希望靠自己的一切努力,挽救回父亲的生命,但老天不饶人啊。
没几天,医生看治疗无望,安排姐姐带着父亲回家,临死前,和家人见个面。但在煤矿上的车送父亲回来的路上,父亲安静地走了,谁也没打搅。待到家时,父亲早已没了气。
父亲走的那一年,我三岁,还不记事。
父亲的离开,对家的打击是无尽的。尽管父亲上班不常回来,但起码,有他在,家里的顶梁柱在 ,家里的魂在,村里人也不敢欺负。
父亲走了,母亲也一下子病倒了,躺炕上不起了。
而大哥,因为内向,但心事特别重。在父亲去世、直到出殡的那几天里,他没掉一滴眼泪,村里人都说他是个傻子,“自己大死了,怎么也不说哭一声?”
但大哥,把失去父亲的伤痛,都深深地埋在了心底,不愿表达出来。那年,大哥也十五岁了。他爱父亲,他比谁都懂得,但他都闷在了心里。
所以,在父亲去世不久,大哥一夜一夜的不睡,在被窝筒里点着煤油灯看书,他希望借此能淡化一点点痛苦。待姐姐半夜里醒来时,发现他依然在看,就催促他把灯吹灭,但等姐姐入睡后,他又点上。
就这样,大哥早早地,就瞅成了近视眼,而且在当年的十一月份,大哥也病倒了。连着发烧,胸腔里憋得喘不上气来。当年冬天,姐姐套着毛驴车,拉大哥到镇上医院去看,也没啥效果,等回来后,已是年关,大哥经过这一趟颠簸,病得更重了,窝在炕上,像一只被箭射穿了的小鸟,只有进气,却没有多少出气了。
出工的人们,在我家墙边上刨冻粪,中间休息,不少人进去看望大哥,一起做工的叔叔,却始终没有进去看上一眼。
正月里,姐姐打听到村里的张盘叔要去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送货,姐姐给人家买了盒官厅烟,求人家顺路把她和大哥捎去。姐姐打听到那边有个公社,叫哈拉沟,有个大夫,看大哥的病,效果挺好。
但在即将出发时,姐姐又受到了阻拦。本村的二夫子老婆,讥笑姐姐,“兰子,你也真是的,多大点病,你又折腾你兄弟呀!年前已经折腾了一回了。”姐姐已经恨透了她,尤其是她家的男人二夫子。
二夫子,是本村的一个保健员,医术不怎么样,却又好喝一口。三年前的二姐,本来得的是脑膜炎,不至于要了命,却因为他酒后的误诊,扎了一夜的过电针,在不到一天的时间,二姐,活脱脱的,正是花一般的年龄,还没来得及绽放,就生生地死在了他的手里。
病恹恹的母亲无奈地和姐姐说,“你有能力,你弄着去吧!我连自己也顾不过来了。”
最后,是姐姐力排众议,斩钉截铁地说,“死,我也要让我兄弟死在外面,也绝不会再死在你二夫子的手里。”
到了哈拉沟,正好又打听到当村里,有个表姐,是母亲这边的亲戚。表姐夫是个民办老师,待人很真诚,也很热情。另外,也是看着大哥,包括我们这一家实在可怜,就除了忙工作,地里的活儿 ,帮着做饭,送饭。
当表姐夫带着姐姐找到这位名医刘晓武(音)时,他给大哥把了把脉。完后,深深地叹了口气,“为什么这么晚才来治?”姐姐意识到了严重,就“扑通”一下,给刘医生跪下了,抱着人家的腿,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求央着,“大爷,求求你,救救我兄弟吧!求求您了!”
“二妹妹没了!大大年前也刚没了!妈妈病倒在炕上,家里连个担水的都没有!看在我们可怜的这个份上,求求您,救救我兄弟吧!”
所有的祸不单行 ,所有伤痛的事,还有自己这些年来的委屈,都涌上了姐姐的心头,她差点儿哭晕过去。
或许是作为医生的责任和使命,或许是姐姐的真诚,感动了刘晓武医生,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答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挽救大哥的生命。
说来,其实,大哥得的是胸膜炎,就是因为心气不舒,内心压抑导致的。而且,姐姐送来时,大哥胸腔的积水几乎已经满了,难怪他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呢。而且,那时,一点儿也不夸张地说,大哥已经瘦得皮包骨了, 十六岁的孩子,胳膊还没有麻杆粗。
刘医生实在是尽心,在治疗中 ,不时地给大哥查体温、查房巡诊,根据每天的病情表现,及时地调整着治疗方案。本来按他的助理的意思,该把大哥胸腔的积水用针管抽出来。但刘医生否决了。他认为,若直接抽积水,大哥的命,可能很快就会没掉。
在刘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和卡拉霉素药物的起效,大哥的胸腔积水,渐渐少了,也不发烧了,呼吸也顺畅了。加上姐姐和表姐一家的精心照料,他也多少能吃进点东西了。
在这些日子里,姐姐一直不分白天黑夜,守在大哥的身旁。大哥打针打的屁股疼,脱不下裤子,是姐姐亲自上手脱;大哥肠干,拉不出来,是姐姐亲自下手,帮他往出抠。失去了父亲的姐弟,苦命情深啊!
在姐姐陪大哥看病,不在家的日子里,母亲只能依靠左邻右舍,还有姑父一家,帮衬着,帮着挑点水,艰难地维持着每一天。待到春天来临时,天渐渐暖和了,母亲也能下地了,多少能干一点儿家务了。于是,姐姐捎信,让母亲去替自己几天。她需要回来带米面,总不能老吃表姐家的呀,他们一家也不容易。
待母亲去了后,只上过半天书坊的姐姐,靠着自己的记忆,加上沿途的打听,四十多里的路程,硬是靠步行,回来了,满脚打的都是血泡。
姐姐在家歇的这一天里,除了准备要带的米面,也听我和二哥寄养在五女子家的妈妈说,“三子,别看小,嘴可甜了。哄得我们特开心。”三子说的是我,我也不知道自己那时为什么那么乖。
姐姐听了,很是欣慰。但是,她歇了一天后,又背着装满米面的布袋子,步行着,又上路了。
好在,经过又一段时间的治疗,大哥得救了,从死神身边,通过不服输的姐姐,拯救回来了。尽管胳膊依然那么瘦,但好歹保住了一条命了。这里,也要特别感谢多年已经失去联系的刘晓武(音)医生,和表姐一家。
…… ……
结 语
现如今,母亲也早早地走了,我们弟兄三个,都已长大成人、立业成家了,而姐姐也老了。因为年轻时,干活受得累太多了,姐姐早早地,就腿疼的不行了,走路一瘸一拐的,靠吃些止疼药缓解疼痛。六十四的人,老得像七十多的了,心脏也不是很好。在二零零五年,姐夫也因胰腺癌去世了。这些年,我们也没能为姐姐做些什么,只是帮扶她的孩子,都工作和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姐姐每每讲起过去,禁不住地,就哽咽了,眼泪也止不住地流。但我知道,姐姐的内心,是幸福的,也依然坚强!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通知我们,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