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pg)
摘要:
放眼19世纪中晚期英国科学发展的宏观图景,作者指出在中国广为流行的“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恩格斯)一说不够全面,对1960年代以来出现的“科学中心转移规律”(汤浅光朝)也提出了质疑,进而尝试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科学状况给出一个更为客观的评价。
撰文 | 刘钝(中国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院长,《科学春秋》主编)
责编 | 艾维
●●●
1 引言
由于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恩格斯的一部论述自然科学与哲学关系的书稿《自然辩证法》,长期以来在中国(以及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被奉为指导自然科学研究的经典,也是从事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研究者们所熟悉的文献,恩格斯在其中一份札记中提到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也被学界普遍接受。本文就针对这一在中国广为流播的说法展开讨论,在充分肯定恩格斯从哲学高度归纳科学发现意义的同时,也针对这一说法的疏漏作了补充说明。
与19世纪的自然科学有关,本文也对在中国学术界颇为流行的另一观点进行了辨析,认为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Yuasa Mitsutomo,1909-2005)于1962年提出的“世界科学中心转移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精致化。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19世纪的中晚期,即汤浅所认定的“德国时代”里,英国仍然在世界科学舞台引领潮流,其最伟大的知识英雄就是分别代表生命科学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与代表物理科学的麦克斯韦(James Maxwell, 1831-1879)。在近代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同时存在着两个或更多的科学研究中心不但是可能的,也是既定的事实。
基于上述两个议题的讨论和分析,作者试图为19世纪中晚期的英国,即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发展状况提供一个宏观的、但相对精确的描述。
2 恩格斯遗漏了什么?

我们现在读到的《自然辩证法》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由恩格斯写于1873-1886年间的10篇大致完成的论文和170多条札记组成。恩格斯去世后,其遗稿先后为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保管。1925年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德、俄文对照的印刷本。在中国,第一个完整的译本出现在1932年,建国后则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主持出版事宜,1971年人民出版社的《自然辩证法》是颇为流行的一个版本,发行量也最大。文革结束后,在于光远主持下,中国学者对书稿作了新的校订,增补了若干资料和注释,又依据恩格斯计划草案的顺序对内容编排作了调整。 许良英曾对恩格斯书稿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清晰的介绍,也被收入这一新编本中。
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大学生大概都读过这本书,“自然辩证法”甚至发展成一门专业的学科,其地位与欧美国家中的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社会学等分支组成的学科群相当; 而作者在书中提到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更是经常出现在形形色色的读本与考卷之中。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三大发现”就是由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注:柯尔丁(1815-1888)是丹麦工程师,与迈尔、焦耳几乎同时从事能量守恒定律的研究,不过他的工作较少为人知道]等人的工作所导致的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施旺和施莱登揭示的细胞秘密,以及由达尔文加以系统论述的生物演化理论。([1], 28-34)
实际上,恩格斯的原稿是一篇以“《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为题的札记,后来被收入《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费尔巴哈》最早发表于1886年,研究者推测这篇札记的写作时间是1886年初。而“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这一标题,是于光远等人在1984年的中文新编本中加上去的([1], 28, 388)。由于《自然辩证法》一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三大发现”一说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可,人们反而不太注意它的出处和恩格斯提出“三大发现”的动机。
应该承认,作为一位非学院出身的政治人物,恩格斯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接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但他十分关注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技术创新,并且以思辨哲学的视角对“三大发现”的意义给予总结。换言之,他的目的是借助自然科学中的最新成果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使得“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哲学的论断,而是自然科学的事实了”;细胞学说揭开了“机体的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而生物演化论证实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并且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系列”。结论是:“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归结到自然的原因了。……因此,比起前一世纪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现在是立足在完全不同的牢固的基础上了。”([1], 30-31)
这一思想在定稿的《费尔巴哈》中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述,恩格斯写道:“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够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4], 339-340)
问题是,在19世纪后半叶,是否还有一些科学成就,在影响人类对世界本质的看法上堪与以上“三大发现”相比呢?
就生物学领域而言,就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至少要比施莱登和施旺等人开创的细胞学说重要得多,那就是由孟德尔肇端的对生命遗传规律的认识。从1856年到1863年,孟德尔在今属捷克摩拉维亚的一个修道院里进行了8年的豌豆杂交实验,从而发现了生物遗传的一些规律。他于1865年完成报告,1866年正式发表文章,但是很久以来没有人认识到其发现的意义。直到1900年以后,他的工作才被重新发现并引起遗传学家们的重视。总之,当时的孟德尔只是一家偏僻修道院中默默无闻的小神父,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恩格斯不知道他毫不为奇。
让我们转到物理学领域,其中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在19世纪中晚期的英国完成的。1831年,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1867)通过实验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又企图借助直观的力线概念加以解释。法拉第事业的继承人麦克斯韦从1855年开始考虑力线观念,1861年提出了磁力线作用的直观模型,尝试用物体周围介质的紧张状态来解释所谓的超距作用;1864年发表《电磁场的动力学理论》,对能量的局域性概念作了精确的阐述——通俗地讲,对于带电和带磁物体来说,能量并非仅仅存留在内部,而且也存在于其周围的空间。从形式上看,麦克斯韦的贡献在于通过一组数学方程式将电场、磁场、电荷密度、电流密度等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电磁场理论。与此同时,他还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并推论光是电磁波的一种形式,进而将具有更久远传统的光学也纳入到经典电动力学的理论框架之中。
曹天予提出以“场纲领”来概括麦克斯韦理论的本体论意义,他写道:“因其非机械的行为而既不同于物质个体,也不同于机械以太。这种新的非机械本体的引入,开创了一个新的纲领——场纲领。” 爱因斯坦在1936年写道:“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电场理论把物理从这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面下解脱出来,这也许是牛顿时代以来基础物理的最深远的转变。”转引这段话的杨振宁评论道:“那个时候已知的两个场论,一是麦克斯韦的理论,一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致力于将这两个理论统一起来。”
杨振宁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麦克斯韦方程组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价也不会过分。麦克斯韦方程就是电磁论。假如没有对麦克斯韦方程的了解,那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世界。直到今天,麦克斯韦方程的深刻含义仍在继续讨论中。”接着他开列出一张直到写作时为止的有关场论的重要进展,包括洛伦兹不变性(1905)、广义相对论(1915)、量子电动力学(1927)、介子理论(1935)、重整化(1947-1949)、路径积分(1948)、非阿贝尔规范理论(1954)、对称破缺性(1960-1964)、弱电理论(1961-1970)、非阿贝尔理论重整化(1971)、超对称和超引力(1971-1976)。 这份清单只开列到1970年代,相信今天的物理学家还可以为它补充大量全新的内容。

►印有法拉第头像的20英镑纸币
统一电磁场理论的最终完成,是培根所提倡的经验传统与伽利略为代表的自然数学化的完美结合,它标志着蒸汽时代向电力时代的过渡,也导致了后来人们对时空场结构与电磁场量子化的进一步认识。麦克斯韦是耸立在经典物理学与现代物理学之间的一座大山,他的电磁关系方程式堪称物理学的“神曲”。如果人们要在牛顿和爱因斯坦之间选择一个人作为顶级物理学家的话,麦克斯韦无疑会获得最高票。
麦克斯韦的电磁学理论和“场”观念逐渐得到科学界承认并被实验证实的时间,正好是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时代。如果说恩格斯所归纳的“19世纪自然科学重大发现”有什么遗漏的话,至少应该补充上麦克斯韦的统一电磁场理论。
3 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巡礼
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群星璀璨,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包括当时尚未独立出去的爱尔兰)都有杰出的科学家和重要的成果[注:如同在文学史、艺术史中一样,这里的维多利亚时代并不严格限定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1837-1901年之间,而是泛指19世纪中晚期的英国]。下面就以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主编的四卷本《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辞典》为基础,分门别类地列出若干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及其成果,对那个时代的科学作一次充满敬意的巡礼,同时也顺带指出一些当时英国科学家著作被引介到晚清中国的情况 。
3.1 数学
英国是微积分的发源地之一。整个18世纪,英国人都沉浸在牛顿光环带来的荣耀之中,而对欧洲大陆的数学进展表现出一种充耳不闻的倨傲态度;与此同时,数学中的伟大创造已经由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陆国家的众多天才们完成了。1815年,几位年轻的英国数学家在剑桥成立了一个名为“分析学会”的小团体,表面是推广在欧陆流行的更为简洁的微积分符号系统,实质是向固步自封的传统提出挑战,呼吁人们正视欧陆特别是德、法数学家在分析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团体的中坚分子是数学家皮考克(George Peacock, 1791-1858)、巴贝奇(Charles Babbage, 1791-1871),以及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 1792-1871)。在他们的影响下,英国数学家开始认真研究大陆前辈与同行们的工作,在若干分支领域重新返回世界前列。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逻辑演算与数学基础方面,除了皮考克外,另一位值得提到的人物是德·摩根(Augustus de Morgan, 1806-1871),他在分析、代数、三角学、四色问题、逻辑代数、数学史等方面均有建树,形式逻辑中有名的德·摩根律也是由他明确提出来的。德·摩根的两本代数学著作在清末被译成中文,那就是由李善兰(1811-1882)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译、上海墨海书馆于1859年出版的《代数学》,以及赵元益与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合译、江南制造局1879年出版的《数学理》,作者的名字则被译作“棣么甘”或“埭么甘”。
在数理逻辑方面值得称道的角色还有不少,首屈一指的或许是布尔(George Boole,1815-1864),一种二元符号运算系统的创始人,以他命名的布尔代数是逻辑运算的重要工具,后来成为设计现代计算机基本电路元件的基础。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道奇森(Charles Lutwidge Dodgson, 1832-1898),其专擅是矩阵代数与数理逻辑,又以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为笔名撰写了两本畅销的儿童读物《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书中隐含了许多数理逻辑与符号代数的知识。还有维恩(John Venn, 1834-1923),他在给剑桥大学的学生们上逻辑课时,发展出一套以若干交叠圆来表达复杂逻辑命题或相应代数陈述的图示方法,被后人称为维恩图或文氏图(Venn Diagram);维恩的工作与布尔、道奇森均有密切关系,在概率论和集合论上也有不少创见。

维多利亚数学家在分析与代数方面的进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表达形式的“改宗”,不过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在数学研究中的影响更为醒目,许多成就具有明显的物理学背景和应用性质。如曾担任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的巴贝奇,除了不遗余力地推广欧陆的微积分成就外,还从事金融数学和科学管理方面的研究,著有《论机械和制造业的经济》、《各种人寿保险机构的比较观点》等;然而真正令他青史留名的却是那个在生前屡遭挫折的分析机的设计和制作――可以说,现代电子计算机的结构几乎就是巴贝奇分析机的翻版,只不过主要元件由传动齿轮换成集成电路而已。
维多利亚数学家在分析与代数方面取得的成就还有很多, 下面只列出一些重要的人物及其工作。首先是每个理工科大学生都知道的格林(George Green, 1793-1841),他成功地将数学分析应用于电磁学,提出位势函数概念,发展出格林积分(牛顿-莱布尼茨公式在平面的推广)。还有发明了四元数的爱尔兰数学家哈密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 1805-1865),当时这一成果如日中天,被时人视为数学物理中最强大的工具,哈密尔顿也被认为是牛顿之后英国最伟大的数学家;此外,他也用数学方法研究天文学和光学,这一点也很像两个世纪前的先贤牛顿。格里高利(Duncan Farquharson Gregory, 1813-1844),研究无穷级数和符号代数,创用符号分离法。还有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数学双子座的西尔维斯特(James Joseph Sylvester, 1814-1897)与凯莱(Arthur Cayley, 1821-1895):前者致力于行列式理论、代数型理论、不变量理论、丢番图分析等;后者的研究领域涵盖代数型理论、不变量理论、矩阵论、椭圆函数、几何学的统一理论等,被认为是哈代之前英国最“纯粹”的数学家。此外还有赫斯特(Thomas Archer Hirst, 1830-1892),专擅射影几何、数学物理;克利福德(William Kingdon Cliffod,1845-1879),在非欧几何、射影几何方面多有建树,提出克利福德-克莱因空间,发展八元数(又称复四元数),创立克利福德代数;以及亥维赛(Oliver Heaviside,1850-1925),致力于无线电波传播的理论问题,从而引入向量分析这一强大的数学工具。

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绝对是维多利亚数学家中的一个异数,他早年从事纯数学研究,后来留学海德堡、柏林,成为英国一流的德国哲学、法律和文学专家。受到生物学家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和韦尔登(Walter Frank Raphael Weldon, 1860-1906)的影响,从1890年代开始皮尔逊将定量方法引入到生物学领域,创建了伦敦生物统计学派,他也成为现代数理统计学的先驱。皮尔逊在数理统计方面的贡献很多,如导出一般化的曲线(非正态)分布,提出χ2分布检验方法,发展相关和回归理论,奠定大样本理论的基础等。皮尔逊又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家,他同情社会主义、支持妇女解放和教育改革。爱因斯坦早年与其“奥林匹亚学院”同伴们选择阅读的第一本哲学书就是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
3.2 天文学
维多利亚时代天文学家的主要成就在于观测和发现新的天体或天文现象,不过有两个人的工作更接近数学家,其中之一是以海王星发现者著称的亚当斯(John Couch Adams,1819-1892)[注:与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Urbain Le Verrier,1811-1877)几乎同时],他还计算了月球轨道,预言狮子座流星雨大爆发;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查理斯·达尔文的次子乔治·达尔文(George Howard Darwin, 1845-1912),他致力于天体演化和地质问题的动力学分析,对地-月系统的演化有深湛的研究。
约翰·赫歇耳可以说是维多利亚天文学家的翘楚,他出身于一个来自德国汉诺威的天文世家,父亲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William, 1738-1822)、姑姑卡洛琳(Caroline Lucrezia, 1750-1848)、儿子亚历山大(Alexander Steward,1836-1907)也都是知名天文学家。他本人致力于南半球星空的观测,发现了众多的双星、恒星、星云、星团等。赫歇耳1847年发表的The Outlines of Astronomy是一本广受欢迎的天文学普及读物,1859年由李善兰、伟烈亚力译成中文,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对于中国人了解西方天文学的历史及新进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书名译得颇为浪漫——《谈天》,作者名则被译作“侯矢勒”。此外,赫氏为《大英百科全书》第8卷所写的“气象”条目也被译成中文,这就是墨海书馆1877年出版的《测候丛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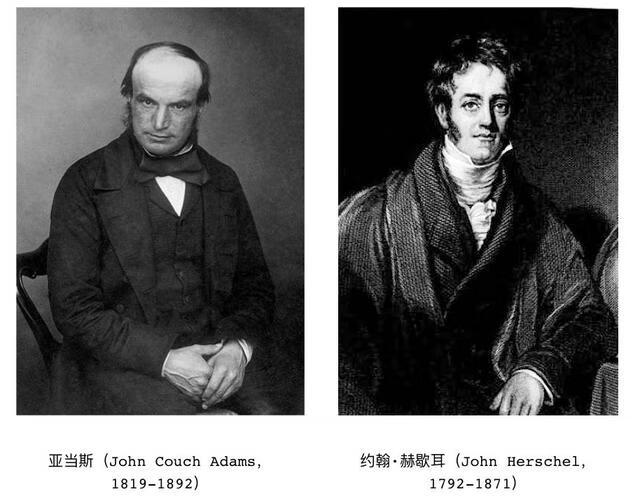
其他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及其成就有:威廉·拉塞尔(William Lassell,1799-1880),发现太阳系行星的众多卫星,如海卫一、土卫七、天卫一和天卫二等;艾里(George Biddell Airy,1801-1892),测量行星轨道,测量地球平均密度,研究二体问题,制定本初子午线及国际标准时;卡林顿(Richard Christopher Carrington,1826-1875),发现太阳闪焰和太阳自转并从事黑子观测,提出太阳黑子出现之纬度呈周期性变化的史波勒定律;普森(Norman Robert Pogson,1829-1891):研究彗星轨道,发现众多小行星及变星,提出星等尺度的“普森比例”;蒙德(Edward Walter Maunder, 1851-1928),发现太阳黑子变化的极小周期。
3.3 物理学与化学
现代原子论的创立者道尔顿(John Dalton, 1766-1844)、电磁学理论的开创者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以及恩格斯提到的焦耳(James Prescott Joule,1818-1889)等,都是公众耳熟能详的人物,此处略过。下面让我们检视其他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力学、数学、地质学、经济学、科学哲学、神学,他也是高产的科学作家、科学组织者和众多新词汇的创造者或提倡者,如“科学家”、“物理学家”、“归纳科学”、“假设-演绎”等,在晚清中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1859年,李善兰与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合作将惠威尔的An Elementary Treatise on Mechanics(1819初版)译成中文,以《重学》为名出版,作者名则被译作“胡威立”[注:后来在中国还有“胡威”、“休厄尔”等译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介绍包括牛顿工作在内的西方近代力学知识的著作。
斯托克斯(George Gabriel Stokes, 1819-1903),大概是麦克斯韦以外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数学物理学家,担任卢卡斯教授长达50年,他的贡献包括流体动力学、弹性力学和光学,由他导出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是粘性流体运动的基本方程组,关于阻力的斯托克斯公式指明了阻力与流速和粘滞系数的关系,微积分中著名的线积分和面积分转换的方法也归功于他。
丁铎尔(John Tyndall,1820-1893)可以说是法拉第的继承人,在当时的英国科学界拥有很高的地位,他又极善演讲,因此被公众视为自然科学的代言人。他在物理学上的主要贡献是研究胶体散射现象,提出丁铎尔效应,进而解释天为什么是蓝色的这样的问题[注:这一曾被广为接受的“标准答案”,被某位不久前过世的天体物理学家断言只是反映了19世纪中叶的物理学水平,对此问题作出更深入研究的是瑞利勋爵,完整的理论则是爱因斯坦在1910年给出的]。丁铎尔在光学、声学、热力学、电磁学和地质学方面也都有所贡献,他的多种著作在清末被译成中文,如《声学》(1874)、《光学》(1876)、《电学纲目》(1881)等(江南制造局亦曾翻译其《热学》一书,但未出版)。在晚清涉及西学的报刊及教科书中,他的名字也屡屡出现,译法则还有“丁达”、“定大”、“定得”、“定得尔”、“田大里”、“田大理”等多种。
威廉·汤姆生,即开尔文勋爵(William Thomson, Lord Kelvin, 1824-1907),他大概是最后一位堪称全能的物理学家,1890-1895年间担任皇家学会会长。汤姆生的研究领域包括电学的数学分析、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流体力学、地球物理、地质学、气象学,又是多种技术的创新者和发明家,在无线电通讯出现之前轰动一时的大西洋海底电缆敷设工程也是由他领导的。除了热力学中普遍采用的开尔文温标外,与其名字有关的科学术语还有开尔文循环定理、开尔文方程、开尔文公式、空间结构的开尔文问题(北京水立方游泳馆的设计与之有关)、开尔文波(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开尔文-亥姆赫兹不稳定性、开尔文-亥姆赫兹发光度、开尔文-焦耳效应、开尔文-斯托克斯定理、开尔文电桥、开尔文滴水管、开尔文测试、开尔文探针、开尔文电报机等。

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 1832-1919),发现第81号元素铊,发明阴极射线管(克鲁克斯管),由此导致人类开始对微观物理世界的探索,又研究空气中固氮问题、稀土元素以及辐射效应等。克氏对矿物学亦有研究,所著A Practical Treatise on Metallurgy详论金、银、铜、锡、镍、锑、铋、汞等重要金属的矿藏、冶炼、提纯及其性质,徐寿(1818-1884)、傅兰雅据此翻译的柯鲁克《宝藏兴焉》即以此书为母本,1884年由江南制造局刊行。
还有,斯博德斯武得(William Spottiswoode, 1825-1883),与其老师丁铎尔一样,斯氏也热衷于向公众讲解科学原理,他的主要兴趣是实验物理,对代数判别式理论也有所贡献,曾于1878-1883年间担任皇家学会会长。斯特拉特,即瑞利勋爵(John William Strutt, 3rd Baron Rayleigh, 1842-1919),研究兴趣包括声学、光学、电学、电磁学、水力学,与拉姆塞一道发现元素氩,与他名字有关的科学术语有瑞利波、瑞利散射、瑞利准则、瑞利-金斯辐射定律与瑞利分布——对后者的质疑导致普朗克提出量子论。菲兹杰拉德(George Francis FitzGerald, 1851-1901),最早提出尺收缩效应(洛仑兹变换的一种形式)。约瑟夫·汤姆生(Joseph John Thomson, 1856-1940),研究阴极射线,提出“葡萄干布丁”式的原子模型,发明磁分离器(质谱仪的前身),他是一位跨世纪的人物,但是其最重要的科学贡献即发现电子是在1897年实现的。
谛拿尔娄(Warren de la Rue, 1815-1889)是出生于法国的著名化学家,研究气体放电,发明了氯化银电池和铂金丝电灯泡,精于天文摄影,连续数年在邱园天文台拍摄太阳表面照片,曾为约翰·赫歇尔拍摄日、月食等天象,被称为天体摄影学的创始人。杜瓦(James Dewar, 1842-1923),化学家兼物理学家,研究原子与分子的光谱,储存液态气体的杜瓦瓶(后来成为日用保温瓶)的发明者。还有拉姆塞(William Ramsay, 1852-1916),他是多种惰性元素的发现者,包括氩[注:与斯特拉特共同发现]、氖、氙、氡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洛克耶(Joseph Norman Lockyer,1836-1920),1868年他在太阳光谱中发现了一条特别的黄线,推测是一种未知的“太阳元素”,因此借用希腊文“太阳”(helios)将其命名为氦(helium),这是第一个在地球以外发现的元素[注:法国人詹森(Pierre Janssen,1824-1907)亦于当年做出同样发现];20多年后,拉姆塞与克鲁克斯证明在一个铀矿中发现的神秘气体就是氦。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1818-1891)在日记中提到的“罗尔门路喀尔”就是他,称其“以光学测天星,制一镜窥火而辨其光气,如着盐即知火中有盐质,着五金之属即知火中有金质。因是以窥星,知某星铁产若干,铜产若干,铅产若干,皆能辨其光气而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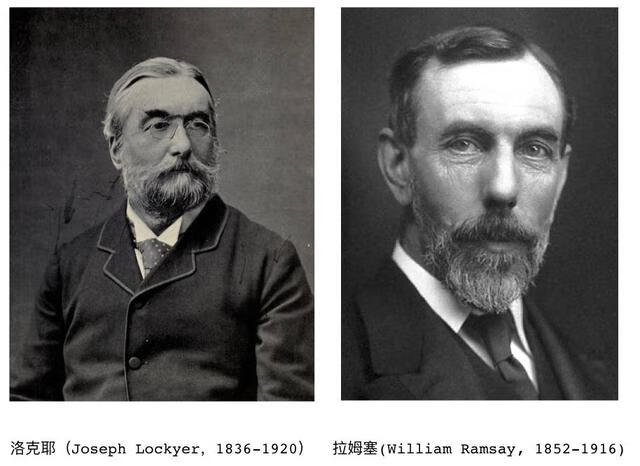
罗斯科(Henry Enfield Roscoe, 1833-1915)是光化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在海德堡大学工作,与德国导师本生(Robert Bunsen,1811-1899)长期合作研究氯、氢在光炽作用下发生反应的情况,发现反应的程度与光的波长有关;他首先析离出金属钒,也是多种化学教科书与普及读物的作者;他为麦克米伦公司撰写的化学教本Lessons in Elementary Chemistry (1866)、Science Primers,Chemistry(1872)在英国销量很大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清末也有数种中译本,如《格致启蒙· 化学》(1880)、《化学启蒙》(1886)等。
阿贝尔(Frederick Augustus Abel, 1827-1902)是军事化学方面的专家,精于制作各种爆炸材料(火药棉、黑火药、无烟火药等),引进“阿贝尔热测试”(Abel heat test)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概念。他与弟子蒲陆山(Charles Loudon Bloxam, 1831-1887)合著的《化学手册》(Handbook in Chemistry,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Technical,1854)在当时颇有影响;后由蒲陆山修订并独自署名出版的《化学》(Chemistry, Inorganic and Organic with Experiments, with a Comparison of Equivalent and Molecular Formulae, 1867)更受欢迎,共发行了11版。1875年傅兰雅、徐寿将以上两书译成中文出版,此即《化学鉴原续编》和《化学鉴原补编》。1869年蒲陆山还出版了《实验室教学或实用化学训练的改进》(Laboratory Teaching 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in Practical Chemistry)。
瑙挨德(H. M. Noad,1815-1877)是电化学家,所著教科书(The Students’Textbook of Electricity,1867)被傅兰雅和徐建寅(1845-1901)译成中文,此即1879年江南制造局出版的《电学》。包曼(J. E. Bowman, 1819-1854)的兴趣是化学工程,其《实用化学入门》也被傅、徐二人选中翻译,此即1871年出版的《化学分原》。
3.4 生物学与医学
维多利亚时代生物科学的焦点自然是达尔文,关于这位科学巨擘的事迹不必赘言,这里只提两位与他的学说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第一位是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他在马来亚半岛考察时发展出生物演化的思想,与达尔文学说的形成几乎同时,两人的成果刊登在同一期的林奈学会会刊上;此外,他还可以称得上是动物地理学的倡导者。第二位是被人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他是达尔文学说不遗余力的宣传者和坚定的捍卫者,自己则是无脊椎动物和古生物学方面的专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科普作家,还曾于1871-1880年间担任皇家学会秘书,1883-1885年间出任会长;除了广为流播的《天演论》外,赫胥黎的另一本通俗科学读物Introduction to Science也被译成中文,这就是艾约瑟等人所译之《格致总学启蒙》,在总税务司署刻印《西学启蒙》(1886)16种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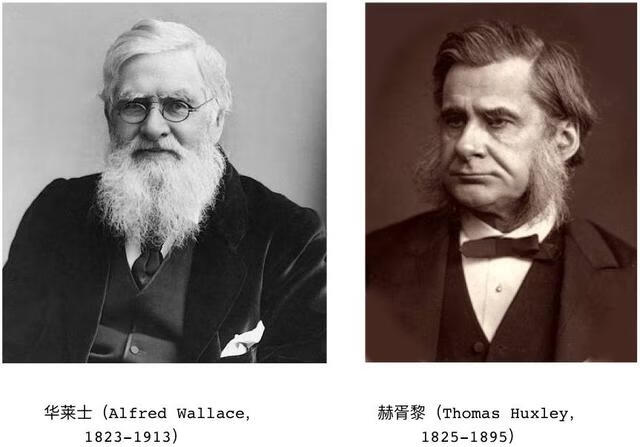
以下出场的人物也都与达尔文有关。第一位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 1796-1861),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老师,正是由于他的介绍后者才有机会参加《贝格尔》号的环球考察。第二位是钱伯斯(Robert Chambers, 1802-1871),他是一位神秘人物,可以说是达尔文的思想先驱,曾匿名发表《自然创造史上的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844),书中激烈批评神创论,提出了自然演化的思想。第三位是达尔文的敌人、比较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欧文(Richard Owen, 1804-1892),他曾长期供职大英博物馆古生物部,促成了英国自然史博物馆的建立,是达尔文学说在科学界的主要批评者。第四位则是达尔文的坚定盟友约瑟夫·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 1817-1911),曾到南极、印度次大陆、新西兰、北非、北美等地考察,研究过美洲及亚洲植物的关系,证明演化论对植物学的实用价值,亦曾多年担任王家园林邱园(Kew Gardens)主任,所著《植物志》是对植物分类学的全面研究,其他著作包括《南极洲植物志》,《新西兰植物志》,《塔斯马尼亚植物志》,《印度植物志》,《邱园引得》等;胡克对中国植物极有兴趣,郭嵩焘在日记中称其为 “虎喀”,又言其“工花草学问,洋言曰波丹尼(botany)”([12],173),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编译的《西学启蒙》丛书中的《植物学启蒙》(1886),就以胡克的著作为底本。第五位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一位兴趣广泛的博学之士,研究领域涵盖体质人类学、生物统计学、心理测量学、气象学、地理学,非洲内陆探险家,更以优生学和指纹学的开创者而留名史册,“优生学”(eugenics)这个词就出自于他。最后是达尔文的三儿子、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 1848-1925),他是一位优秀的植物生理学家。

►印有达尔文头像的10英镑纸币
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一些著名生物学家或医学家还有:布朗(Robert Brown,1773-1858),主要从事澳洲植物考察,1827年观察到悬浮在水中花粉的无规则运动[注:1905年爱因斯坦根据扩散方程建立了布朗运动的统计理论];威廉·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1785-1865),植物学家,园艺学家,曾任邱园主任,约瑟夫·胡克之父;曼特尔(Gideon Algernon Mantell,1790-1852),恐龙化石的发现者;林德利(John Lindley, 1799-1865),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和园艺学家,他的《植物学》(Elements of Botany,1841)由李善兰、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等人合译,1859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是为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书;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外科消毒法的发明者,挽救了无数战争中伤员的性命,亦曾担任皇家学会会长(1895-1900);汉斯(Henry Fletcher Hance, 1827-1886),中国植物分类学的权威,胡克父子在中国的主要联系人;谢灵顿(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 1857-1952),研究生理学、病理学和细菌学,提出神经反射学说;贝特森(William Bateson,1861-1926),胚胎学家,孟德尔学说的坚定支持者,遗传学(genetics)一词就是由他创造的。
3.5 地质学与地理学
由于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的刺激,海上探险和域外考察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时尚,探险归来(或壮志未酬)的英雄如同做出重大发现的科学家一样受到社会的尊重,相关的地质学和地理学(包括水文、洋流、气象等)也都得到很大的发展空间。
首屈一指的地质学家当然是赖尔(Charles Lyell, 1797-1875),他提出的地球演化史(渐变论)对达尔文学说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著有《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 Being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Former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 by Reference to Causes Now in Operation,1830-1833)、《人类古代的地质学证据》(The Geological Evidences of Antiquity of Man, 1863)等,前者是达尔文乘坐《贝格尔》号环球考察时经常阅读的书籍。清末华蘅芳与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more MacGown, 1815-1893)曾合译过一本《地学浅释》,原本是赖尔的另一本较为通俗的读物Elements of Geology,该书初版于1838年,玛、华所用母本是1865年的第6版,故此其中提到了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这一中译本于1871年由江南制造局刊行,作者名字则被译作“雷侠儿”。

著名的地质学家还有塞吉威克(Adam Sedgwick, 1785-1873),他也是达尔文的老师,不过对自己学生提出的“自然选择”理论抱着怀疑态度;麦肯尼·胡斯(Thomas McKenny Hughes, 1832-1917)则是塞吉威克的学术传人,精于岩石、矿物鉴定;盖基(Archibald Geikie, 1835-1924)是河流侵蚀理论的提倡者,所著《野外地质学纲要》(1876)、《地质学教程》(1882)、《地质学奠基者》(1897)使其在西方地质学界享有盛誉,他为麦克米伦公司撰写的普及读物也被译成中文,是为《地学启蒙》。
地理学家威廉姆·胡斯(William Hughes,1818-1876)著有制图学著作Manual of Mathematical Geography (1852),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1839-1914)、王德均将其译成中文,1875年由江南制造局刊印出版,中文作《绘地法原》,此乃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西方投影制图术的专著。
著名的旅行家和地理学家中,名声最响的是在非洲内陆探险的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和伯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1821-1890):前者“发现”了维多利瀑布、马拉维湖等,寻找尼罗河源赍志而殁;后者“发现”了坦噶尼喀湖等。后来的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沿着列文斯通的足迹深入非洲腹地,最终揭示了列文斯通“失踪”的真相。此外,还有从事北极探险的富兰克林(John Franklin, 1786-1847),以及从事南极探险的斯考特(Robert Falcon Scott, 1868-1912)和沙克尔顿(Ernest Shackleton, 1874-1922)等。他们的工作丰富了西方人对地球表面的认识,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地理学的又一次飞跃。
4 汤浅观点质疑,兼从制度层面看维多利亚科学
1962年,神户大学的科学史家汤浅光朝在英国人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 1901-1971)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科学技术编年表》等文献资料,采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科学中心转移论”。其大意是:16世纪世界科学的中心在意大利,即文艺复兴后伽利略的祖国;17世纪科学中心转到了英国,也就是皇家学会与牛顿等人登场的舞台;之后是启蒙运动直到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从1810年至1920年德国开始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一战之后直到今天则是美国科学执世界之牛耳。

也就是说,整个维多利亚时代,世界科学的中心都在德国。本文的目的不是对汤浅光朝的理论进行全面的评述,也不否认德国科学在19世纪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并走向世界前列。袁江洋已经指出以汤浅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科学计量学在研究过程中缺乏对诸多难以量化的因素、特别是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并预设了一些可疑的前提;此外,在汤浅那个时代,科学计量学所依赖的基本数据库也远远没能达到足以进行精确分析的条件。他还特别指出:“英国科学技术体系是经由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体制化的”,“自18世纪直至今天,英国一直是世界上主要的技术输出大国”,“无论如何,不能认为自1730年以后,在这个孕育了达尔文和麦克斯韦这样划时代的科学人物的国家里,科学事业辉煌不再”。
实际上,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是1871年以后才出现的,从1810年到1920年长达110年的时间段里,德意志经历了一个从相对落后的诸多封建王国(或侯国)组成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向统一现代国家的转型,但是就政治制度的设计与社会文化事业的基础而言,它与经营了数百年的大英帝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汤浅以1810年作为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起点,可能是将研究型大学的出现作为参考依据;而以1920年作为终点,显然是要撇清德国科学与希特勒崛起的干系。这两个节点的选择,或许透漏了某些“可疑的前提”的蛛丝马迹。
维多利亚时代、特别是她的鼎盛时期,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经济持续增长,君主立宪制进一步完善,社会相对稳定与繁荣。在英国人的精神生活方面,经验主义与清教传统依然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由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等人提倡的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日渐深入人心,又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鼓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磨砺激荡,追求财富与成功、推崇聪明与才智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从事科学研究也成了无比光荣的人生选择,甚至“科学家”(scientist)这个词也诞生于这个时代。就维多利亚科学而言,如同其社会、政治与文化一样,主要特征是全面、持续的繁荣与累积性的进步,以及不断完善的制度为其领跑地位提供的保障。下面就通过一些特殊的例子对此观点加以说明。
这里首先要提一下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考试制度(Mathematical Tripos)。这一起源于18世纪中叶的考试,初衷是改变传统人文教育中以拉丁语辩论为优胜依据的做法,而代之以书面形式的数学答卷作为衡量学生智力的重要标准。1847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出任剑桥大学校长,他极力主张加强数学与自然科学在大学教育中的比重。在他主持通过的大学改革方案中,提出将电、磁、热等内容增加到Tripos考试的范围。皮尔逊(他自己参加了1879年的考试并获得第三名)认为:“昔日的Tripos是一种优秀的考试制度,理由之一是它不局限于特殊的知识,而是提供一个包括许多数学科学分支基本原理在内的一般图像,理由之二是它迫使教学者强调‘问题’在数学中的意义”。另一位当代的研究者通过对Tripos试题的分析,发现维多利亚时代剑桥大学的数学教育非常重视代数与分析技巧的运用,强调数学与天文学、物理学的联系,因此对19世纪后半叶数学物理在英国的兴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Tripos考试的特点是难度大、题目多、时间长。以1854年为例,试卷多达16张纸,共211道题,要连续考8天,总计44.5小时。每年的考试也成为那些古老学院暗中较力的战场,在评议厅举行的发榜仪式更成为当地的一件盛典。成绩最好的那些考生被称为Wranglers,头名则是Senior Wrangler。优胜者的名单会出现在《泰晤士报》上,那些荣登榜首的数学天才一夜之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Wrangler称号也意味着很多机会,至少被学院接受为研究员(fellow),日后多数人成为数学或物理学教授,也有些人当了法官、律师、牧师或医生。Senior Wrangler也成为“学术至尊”(Academic Supremacy)的同义词,如同中国今天的“院士”一样。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剑桥数学状元包括约翰·赫歇尔(1813)、艾里(1823)、斯托克斯(1841)、凯莱(1842)、亚当斯(1843)、瑞利勋爵(1865);获得第二名的则有皮考克(1813)、惠威尔(1816)、开尔文勋爵(1845)、麦克斯韦(1854)、乔治·达尔文(1868)和约瑟夫·汤姆生(1880)等。
成立于1660年的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是最早出现的科学组织之一,也为后来一些类似的机构提供了示范,然而它更像一个汇聚社会精英的象牙塔。到了19世纪初叶,由于会员年龄的老化与贵族成员的增多,这一老资格的科学组织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30年代遭致巴贝奇等科学新锐的严厉批评。与之相比,成立于1799年的王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的活动则更贴近普通民众。特别是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在法拉第、丁铎尔、杜瓦和瑞利勋爵担任实验室主任的时候[注:研究院历任院长均由具有社会声望的贵族担任,负责学术研究的是实验室主任],王家研究院举办的科学讲座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由法拉第创出名牌的“圣诞演讲”成为年终的一个重大社会新闻,法拉第和丁铎尔师徒两人分别主持了19次和12次圣诞演讲,当时的报刊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一机构的活动与种种新发明。

►1856年法拉第在王家研究院作有关力学的演讲(《伦敦新闻画报》)
前排正中坐着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君阿尔伯特亲王和两个小王子

►1869年丁铎尔在王家研究院作有关电学的演讲(《伦敦新闻画报》)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之后,在社会上和思想界都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为了反击宗教势力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中伤、维护科学研究的自主性,一批志同道合的科学家认为应该对皇家学会加以改造,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X俱乐部的非正式团体,从1864年11月到1893年3月,除了夏季的三个月以外,每月聚会一次,地点在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餐厅,时间通常在皇家学会会议开始前2小时。赫胥黎是X俱乐部的灵魂人物,其他重要成员包括生物学家约瑟夫•胡克、物理学家丁铎尔、斯博德斯武得、哲学家斯宾塞、数学家赫斯特、化学家弗兰克兰德(Edward Frankland, 1825-1899)、外科医生兼动物学家巴斯克(George Busk, 1807-1886)、银行家、慈善家兼博物学者卢伯克(John Lubbock, 1834-1913),后者是老达尔文的忘年交和在Down House的邻居,也是X俱乐部的重要资助者。19世纪70-80年代是X俱乐部最活跃的时期,从1873至1885年,胡克、赫胥黎、斯博德斯武得相继担任皇家学会主席,对于这一科学组织摆脱贵族与宗教势力的影响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大约与此同时,《自然》杂志开始艰辛的创业过程,它的创始人和首任主编就是那个在太阳光谱中发现氦元素的天文学家洛克耶。X俱乐部的成员多是这一刊物的早期作者,他们提倡自由主义精神,反对宗教权威,鼓吹科学进步论,同时也积极地介入社会与公众生活。
除此之外,各种专业的学会在维多利亚时代也十分活跃。特别是随着海外扩张与殖民政策的实施,人类学、考古学、博物学、地质学、地理学、水文学、海洋学等学科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皇家地理学会、皇家地质学会、皇家园艺学会、林奈学会等专业学会的活动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成立于1831年的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现改名为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其初衷是对抗皇家学会的贵族气和官僚气,后来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跨行业科学组织,并与科学界的精英们维系着良好的关系。科学促进会的一大特征是每年在不同的城市举行年会,目的是扩大科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以其名义组织的最成功活动包括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威伯福斯的辩论(1860,牛津)、丁铎尔关于生命可能来自无生命物质的演讲(1874,贝尔法斯特)等。

►化学家罗斯科在英国科学促进会伯明翰年会上演示镁光灯摄影(《伦敦新闻画报》,1865年)
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也出现在维多利亚时代。1861年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亨利·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1731-1810)的后人、德文郡的威廉公爵成为继任,他于1871年捐资创建了一座现代物理实验室,以纪念自己的科学家先辈,麦克斯韦则被聘为首任卡文迪什教授。在麦克斯韦之后继承这一教席的是瑞利勋爵、约瑟夫·汤姆生,直到后来的卢瑟福与劳伦斯·布拉格。140年来,这一实验室对近代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至于与科学关系密切的工程和技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在世界的领先地位更是明显它们与专利法、公司法等社会制度的关系尤为密切,限于篇幅本文就从略了。
5 结语
恩格斯主要是一位政治人物,尽管具有较深的哲学造诣并对同时代的自然科学进展怀有浓厚兴趣,他在一篇学习札记中的言论不应该成为科学史研究的定论;同样道理,《自然辩证法》这部未完成的论文集,也不可能作为当今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的理论指南[注:顾准认为,“把《自然辩证法》从草稿里硬挖出来……那是一场悲剧。德波林这种‘后退’的逆流,是想抬出恩格斯增加哲学的权威,要用哲学来指导一切]。
汤浅光朝论点的依据是统计数字。他以几本辞典类的读物为基础,对同一时期世界各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加以打分。这一研究为科学计量学提供了一个示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科学中心演变的趋势。然而在他那个时代,科学计量学所依赖的基本数据库尚不完备,他的评分也更多地看重数量而忽略了质量,因此在今日看来难免显得粗糙一些。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国力傲视群雄,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科学群星辉耀,技术创新迭出。何况维多利亚英国还出现了绝世无双的达尔文,又有足以继承牛顿交椅而开启爱因斯坦圣殿的麦克斯韦。这两位都是超一流人物,超一流是世不二出、独领风骚数百年的角色。借用天文学家普森对可视星亮度的分级标尺,将肉眼能看见的最暗星定义为6等,最亮的星是1等,1等星与2等星之间的亮度比是2.5,而6等星的亮度仅相当于1等星的1%。苏联物理学家朗道制定的智力分野更为鲜明,他认为一流物理学家的贡献比二流多10倍,而爱因斯坦那样的超一流与二、三流物理学家的差距则非道里可计。

如同科学探究一样,科学史的研究同样需要立足于实证的材料,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综合,而不以权威或书本上的成说为依据,这样方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中国的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持续发展,这一现象在人类近代史上或许只有维多利亚时代盛期等少数的历史阶段可资比较。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人们追寻强国梦的心情就显得格外急迫,社会文化层面上一些值得珍视的观念反而被忽视了。在笔者看来,与其整天空泛地讨论何时能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何时能拿到诺贝尔奖,何时能建成牛津、剑桥一样的世界名校,何时能培养出达尔文、麦克斯韦那样的大师级人物,不如认真地研究一下那些成功的历史经验。科学繁荣不可能由个别天才在短时间内营造出来,科学革命也只有在常规科学的长期积累和持续进步的基础上才会出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科学全面而持续的发展,与其相对和谐的文化环境与相对合理的社会设计,特别是不断完善的科研制度之间的关系,应该引起人们的更多关注。
原题为《维多利亚科学一瞥——基于两种陈说的考察》,载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年第34卷第3期,此为最新节略修订本。
参考文献:

欢迎个人转发到朋友圈,
copyright@zhishifenzi.com
科学春秋
在科学中寻觅历史
在历史中思索科学
微信ID:kexuechunqiu
投稿kexuechunqiu@sina.com
授权copyright@zhishifenzi.com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通知我们,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











